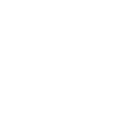内容提要:我国目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浪潮纯粹是贼喊捉贼、李鬼捉李逵的闹剧。这场闹剧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逆流,中华文化发展史的耻辱,是我国学术界的雾霾,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股逆流在中国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必然产物。必须从哲学、科学学的高度对这股逆流迎头痛击以正本清源,还我国科学界以朗朗乾坤,使我国科学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科官科伪科学教育产业化科学范式科学发展
“借反伪科学之名而反民科”纯属学贵派作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出现了一股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思潮。该思潮的本质特征,是先通过把民科和伪科学划等号、原创理论和民科划等号,然后把原创理论和伪科学划等号。不管谁,只要提出原创理论,先给你贴上“民科”标签然后扣上“伪科学”帽子进行攻击。
那种看到有谁提出原创理论先进行头衔身份考察,一旦从网络上捕风捉影发现对方是“民科”就如释重负大喜过望,呼朋唤友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的大呼小叫,似乎捞到的不是一般稻草而是救命稻草,似乎抢占到了身份制高点并因而抢占到了学术制高点,进而欣喜若狂的犹如打了鸡血那般手舞足蹈,张牙舞爪的摆出一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架势,“大义凛然”欲把其清除出局的“现象”;
那种民科是伪科学——某人是民科——某人的原创理论是伪科学的通行逻辑,那种体制外不如体制内、民科不如官科、非科班不如科班、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认为只要把比自己先进的科研成果贴上“民科”标签扣上“伪科学”帽子,就可以若无其事旁若无人躺在沙发上、夹着二郎腿抽着烟品着茶优哉游哉的眯着眼锁着眉、盘算着怎样向国家申报选题套取国家科研经费、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继续自我陶醉于早已被“民科”甩掉几条街的课题研究的“学贵做派”;
那种对“民科”抱“种族歧视”,认为只有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系统内自我循环近亲繁殖对“民科”进行“种群隔离”,才能避免“民科”基因污染培养出纯而又纯的纯种科学家的“门户观念”;
那种自己技不如人却在反民科反伪科学名义下,设置种种似是而非的进入障碍,抱残守缺削足适履的阻挡科学发展,以维护旧的范式共同体成员的狭隘学术既得利益、包括学术话语权不当垄断的机制设计;
那种在反民科反伪科学名义下,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学历评价高于学术评价、把学历评价作为学术评价的必要前提,规定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必须有博士学位、使不赚钱的学术体制成为能赚钱的教育体制的附庸,以保证教育产业迅速发展高校利润迅猛增长的“制度设计”;
凡此种种,不但彻底关闭我国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而且造成我国学术教育公共品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位;不但误人子弟,而且严重败坏了我国学术风气,破坏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果断停止民科和伪科学划等号、官科和科学划等号、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制度体制机制设计,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开发作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价值观导向。必须认真剖析我国当前反“民科”思潮的成因与危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将民科与伪科学划等号”是学术话语权的别有用心
民科的本义就是民间科学家。伪科学,是已经被实践(包括科学实验)证伪、但仍然当做科学予以宣传推广的理论假说或假设。在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理论假说或假设往往是科学发现的拐杖。实践证明,科学史上的假说或假设95%是错的,但不能由此否定假说或假设(包括被证伪的假说或假设)在人类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理论假说或假设本身就是伪科学。
只有理论假说或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情况下,仍然将错就错当做科学予以推广的,才可以认定为伪科学。在理论假说或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情况下,提出者没有将错就错继续把该假说或假设当做科学予以推广,社会上仍然把该假说或假设当做伪科学甚至科学骗局穷追猛打,将挫伤科学家或科学爱好者科学探讨的积极性。
如果把伪科学和某种特定身份如民间科学家划等号,则是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手段;在把不是伪科学当做伪科学进行攻击的同时,为真正的伪科学开绿灯。如果说,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西方经济学可以作为假说而存在,那么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后,再宣传推广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就成为伪科学。
从上述民科和伪科学的概念本义中,看不出民科和伪科学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本来,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应该在揭示“民科”和伪科学概念的内涵外延的基础上明确说明“民科”和伪科学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很遗憾,目前没有一个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什么是民科?民科就是伪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伪科学就是民科——这就是反“民科”者的基本逻辑。
不过根据本人的观察和概括,“民科”一开始系指我国体制外、非官方的民间科学家,但后来逐步延伸为泛指所研究课题不属于自己所学专业领域或在所研究领域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民科”概念的实质不是一种对科学家群体的分类,而是把“民科”和“伪科学”划等号的学术评价,因此“民科”是贬义词。由于人类历史上大量的第一流的科学成果都是民间科学家取得,当今量子时代真正的第一流科学成果往往是跨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研究的成果,任何科学成果都是科学家或科学爱好者无身份约束条件下认真观察深入调查苦苦思索大胆设想反复验证的结果,把“民科”和“伪科学”划等号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没有科学学根据。之所以“民科”和伪科学之间能建立起某种内在关系,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民科”概念作了内涵延伸和外延扩大。
对科学“特殊人群”的狭隘定义缺乏基本科学常识
在我国,所谓民间科学家就是指的体制外的科学家;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只有中国才有,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
如果只有体制内的科学家才属于“科学共同体”,体制外的民间科学家就属于“在科学共同体之外”,那岂不是说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都属于“在科学共同体之外”?
如果科学共同体的内外标准不是体制内外,而是另外的标准,那又怎么能把“民科”“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民科”难道不是“民间科学家”的缩写吗?在中国“民间科学家”难道不是指体制外科学家吗?
如果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不是指的体制外的“民间”科学家,那么这对“民科”下的定义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给概念下牛头不对马嘴、形式脱离内容的定义纯粹就是偷换概念的胡扯蛋。那么请问,给概念下牛头不对马嘴、内涵模糊逻辑混乱纯粹胡扯蛋的定义,是哪个“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难道给概念下胡扯蛋定义的“工作”“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吗?
人类科学发展过程就是范式转换过程;与范式转换过程相对应的,总体上就是旧的“科学共同体”瓦解、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的过程。旧的“科学共同体”瓦解、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的过程和范式转换过程虽然是对应的,但不是同步的——范式转换意味着旧的“科学共同体”瓦解、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但不等于和旧的范式转换、新的范式形成的同时,就能在新的范式基础上马上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从新的范式出现到新的“科学共同体”建立之间必然会出现一个在旧的“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就是这些“特殊人群”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的雏形。
把这些“特殊人群”定义为游离“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民科”、“伪科学”,实际上是否定了人类科学发展过程是范式转换的过程。这不符合科学史的事实。同时,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建立在不同范式基础上,所以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是正常的。相对论刚产生时,爱因斯坦被德国物理学界斥责为“疯子”;而爱因斯坦本人也至死不承认量子力学。是否意味着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创始人都是民科和伪科学?
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不能否定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过程就是由“不能达成基本交流”的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转化组成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就是由牛顿力学向量子力学转化的中间环节,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和宇观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是一般均衡理论,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是对称平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对称平衡理论也“不能达成基本交流”,但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的西方经济学向以对称平衡理论为“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的对称经济学转化,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所以人类科学史就是“不能达成基本交流”的具有不同“特定思维方式”、不同“基础范式”的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转化史。那些把具有不同“特定思维方式”、不同“基础范式”的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官科和民科、科学和伪科学的关系,说明缺乏基本的科学史知识与科学学常识。
“民科”与“官科”的悖论之辩
如果“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不是学科范式概念,而是指的科学学的基本原理,那么所谓的“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也不是什么“民科”,而是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不符合科学学基本原理的“特定思维方式的人”。很遗憾,“科学研究不符合科学学基本原理”的“特定思维方式”的人不但“民科”有,“官科”也有。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所以严格意义上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是理论的原创性。
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原创程度高低与学术水平高低、实践价值大小、学者的学术地位成正比。这应该是学术评价中“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那么现在高校推行的什么“论”都有,唯独没有“原创论”的“科班论”、“民科论”、“官科论”、“刊物级别论”、“核心期刊论”、“SCI收录论”、“评奖级别论”、“双顶级论”、“影响因子论”、“论文引用率排名论”、“同行评价论”的学术评价标准,这是否属于“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
如果是,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高校被“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的“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所把持?如果不是,那么“科班论”、“民科论”、“官科论”、“刊物级别论”、“核心期刊论”、“SCI收录论”、“评奖级别论”、“双顶级论”、“影响因子论”、“论文引用率排名论”、“同行评价论”的学术评价标准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的科学学或科学史依据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应以原创基础理论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现在高校推行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如果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就要先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世界顶级刊物”的概念定义是什么?如果说,“世界顶级刊物”就是发表“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的刊物,那什么是“世界顶尖科研成果”?如果又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作为“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的定义,岂不是犯了定义项包含被定义项的逻辑错误?
2、评定“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评定“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就是发表的论文都是“世界顶尖科研成果”,那么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作为“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岂不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3、如果以刊物的影响因子大、所发表论文的引用率高作为“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那么评估刊物的影响因子大小、所发表论文的引用率高低的参照系是什么?如果评估刊物的影响因子大小、所发表论文的引用率高低的参照系是美国或英语世界,能够用美国或英语世界的影响因子大、论文引用率高作为“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吗?
4、即使以全世界为参照系,以影响因子大、引用率高作为“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圣经》在全世界的影响因子最大,引用率最高,能不能说圣经就是科学?《资本论》在全世界的影响因子、引用率仅次于《圣经》,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
5、“世界顶级刊物”的标准是谁制定的?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人,他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资格谁赋予的?赋予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资格的人,他赋予制定“世界顶级刊物”标准的人的资格的资格,又是谁赋予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是我国高校以“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还是笔者主张的以原创基础理论作为“顶尖科研成果”的标准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
笔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的博士,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在世界一流大师指导下把学生培养成能出世界一流成果的一流人才。
而目前中国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是西方名牌大学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破格提拔教授、博导;西方名牌大学经济学毕业博士+“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或《经济研究》发表几篇充满数学模型的经济学论文=破格提拔经济学教授、博导。北大清华甚至规定应聘北大清华教授必须是“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必须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可是不少“世界顶级名校”毕业经济学金融学博士博导终身教授、能够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排名很靠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连经济学金融学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束手无策,既不能解释又不能解决,说明“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既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不是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
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却没有任何真正学术建树、既没有原创理论又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二三流三四流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信口开河,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指点江山,使之在中国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话语权与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整个社会不公平,严重误导了人才的成长,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那么,是笔者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还是目前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如果认为目前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那么目前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后面的科学学原理是什么?如果认为是笔者的标准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那么岂不是笔者的是官科,而中国的高校都是民科?
中国的大学讲台被西方话语权控制
北大清华等高校自主办学主体把西方当国际、美国当世界、美国大学当世界顶级名校、美国出版的刊物当国际顶级刊物、美国刊物发表的论文当世界顶尖科研成果、美国学术界对论文的引用率排名当学术评价的标准,把中国人的学术话语权拱手让给美国人,并美其名曰“与国际学术评价标准接轨”。
实践是检验各种学术头衔、学术标准含金量的唯一标准。符合北大清华“双顶级”标准、掌握中国经济学领导权话语权、也是“双顶级”标准的提出者与设计者和靠所谓“双顶级”标准来引进世界一流大学方案设计的始作俑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者,虽然榜上有名,台上有声,媒体追踪,光彩照人,在中国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话语权、影响力与市场价值,但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领域除了大力宣扬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社会货币化外,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产能过剩、产业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现实经济问题上谈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见解;相反,他们极力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社会货币化与GDP增长方式却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
事实证明,所谓的“双顶级”并不是真正的顶级;“双顶级”选人标准并不是真正的高标准严要求,而只是承载高校自主办学主体狭隘利益的西方话语权对中国话语权的一种恶性竞争、不当竞争,其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使中国的大学讲台被西方话语权控制;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毕业的美国大学自封为“世界顶级大学”,把给自己发表文章的西方刊物自封为“世界顶级刊物”,是为了使自己对北大清华讲台的垄断和对中国经济学话语权的控制合法化。
有关方面之所以给“双顶级”主流经济学家极高的学术地位、话语权乃至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领导权,是为了强化他们头上的“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的光环对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示范效应与推动效应;让他们整天在电视上晃来晃去,实际上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开发成教育产业的客户,让他们为教育产业当模特做广告。这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也是对中国人民扭曲的价值观、个人成长观导向。自己没有任何原创理论、所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又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顶着西方名校经济学博士和“著名经济学家”头衔、掌握高校办学自主权、极力鼓吹推行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
泡沫GDP、教育向钱看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践踏中国人民的创新成就,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名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北大清华等高校自主办学主体推行的学术体制学术标准很难说符合哪一条“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
民科不是伪科学,“民科”概念才是伪科学
违背科学学基本原理或“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只是一种行为,和特定的主体之间既不能划等号也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把违背“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或违背科学学的基本原理这一行为和特定的主体“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划等号、然后又把“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和“民科”划等号是牵强附会的,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根据,而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偷换概念把违背科学学的基本原理或“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即“特定思维方式的人”和“民科”划等号,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间科学家,达到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目的。
指责“民科”研究不规范,自己却无法给“民科”下个符合科学学规范标准、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定义,必须由“研究不规范的”民科自己给“民科”下个符合科学学规范标准的定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说明,反民科思潮本身违背了“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不是违背某个具体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而是违背了科学学原理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如果说,违背某个具体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有可能是新理论的产生、科学的发展,那么违背了科学学原理的“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则只能是伪科学。
因此,民科是伪科学,某人是民科,所以某人的原创理论是伪科学这样的逻辑不成立。“民科”概念纯粹是有完整学历却没有像样学力纪录、高分低能技不如人的无能之辈用可怜的身份自尊掩盖身价自卑、用曾经考场上的辉煌掩盖现实成就的尴尬、掩盖自己无能取得心理平衡的通道和进行恶性竞争以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工具。
民科不是伪科学,“民科”概念才是伪科学。那些声嘶力竭歇斯底里对“民科”口诛笔伐的人没有一个有原创理论,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原创理论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对称逻辑是伪科学?因为笔者是民科,学界无名,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因为对称逻辑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国外网站也查不到;因为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课本里也没有出现过。官科、学界有名、老师讲过、课本里出现过、国外网站能查到的,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就是反“民科”者的科学素养。
恩格斯说:一旦社会上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将比十所大学更快推动科学的发展。我国自古就有“真正的高手在民间”的说法,科学艺术发展的真正源头是社会实践,高校和社会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高校的创新动力与创新灵感离不开社会的创新氛围与创新需要,国民创新体系离不开全社会的创新机制。创新驱动型经济是国民创新体系的经济基础,国民创新体系是创新型大学的社会基础。创新型大学与创新型国家的人才、机制、成果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创新型大学实际上是创新型国家的“全息元”。没有民科的蓬勃发展,创新型大学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国“民科”和“官科”的现状与未来:学历完整性、职务正规性、头衔显耀性、身份显赫性、待遇优越性、学风浮躁性,“官科”优于“民科”;理论原创性、知识系统性、逻辑严密性、学风严谨性、学术规范性、实践有效性,“民科”优于“官科”。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拥有大学讲台、掌握学术话语权、占有媒体宣传制高点、攻城略地大奖小奖各种荣誉地位统统拿下的,“官科”优于“民科”;真正能创立原创基础理论、改变人类历史、在人类科学史上刻下痕迹青史留名奠定中华民族学术地位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不是目前风光无限的“官科”而是暂时默默无闻的“民科”。
“学风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
在我国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民科是伪科学—某人是民科—某人的原创理论是伪科学,这样的逻辑能够在社会上通行很难说真的仅仅是出于反“伪科学”。如果真的仅仅是反“伪科学”没必要把“伪科学”和“民科”——特定身份捆绑在一起,没必要把“伪科学”和“民科”两个概念划等号。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要害与危害在于:不是用原创理论检验博士学位是否合格,而是用博士头衔衡量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用颠倒的学术评价标准抬高学历贬低学力;在高分低能的假“博士”在真学力面前相形见绌、证明教育产业化政策已经失败的情况下,通过“民科”“官科”的二元区分、颠倒学术评价标准以继续掩耳盗铃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是以合法名义掩盖非法目的,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实质是高分低能的假“博士”对真学力的挑战。
“民科”概念的产生、极具中国特色的“民科”“官科”的区分、反民科思潮的出现,说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极度缺乏科学素养,说明我国教育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学风问题。但在我国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不仅仅是学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教育产业化政策及与之相应的逆选择逆淘汰的干部人事制度环境下,学历和学力、头衔和水平、身份和身价的不对称乃至巨大反差是必然的,也是普遍存在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
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学历和学力、头衔和水平、身份和身价不对称的尴尬现实面前,有关方面如果不是通过学术体制、教育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实现优胜劣汰,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实现学历和学力、头衔和水平、身份和身价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实现学历和学力、头衔和水平、身份和身价的高层次平衡以消除社会异化现象,而是将错就错通过把科班和科学、学历和学力、“民科”和伪科学划等号的政策、体制、机制设计与价值观导向强制实现学力和学历、水平和头衔、身价和身份的低层次平衡,就为反“民科”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体制保证、舆论环境与社会心理基础。在反“民科”浪潮中跳得很高的人,实际上都是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的马前卒。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车轮不可阻挡,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从科学发展观来看,任何强制实现学力和学历、水平和头衔、身价和身份低层次平衡以维护现有的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教育产业化政策与逆选择逆淘汰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措施,都只能捉襟见肘、顾此失彼、贻笑大方,在人类历史上落下以纸包火、削足适履、抽刀断水、螳臂当车的笑柄。如果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而一手遮天倒行逆施刻意扭曲颠倒人类文明价值体系,用“官科民科”的区分固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那就不仅仅是异化和笑话,而是反人类。
“知识诚可贵,学分价更高。只要拿文凭,两者皆可抛”,“60分万岁,70分受罪”,很难想象在这样被动学习的环境中能培养出具备出世界一流的原创成果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很难想象经过这样的被动学习形成的“学历”和“学力”、“科班”和“科学”能划等号。沉湎于“科班”和“科学”、“民科”和“伪科学”划等号的幻觉中不可自拔的现行高校自主办学主体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卖学分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除了读教科书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造成我国大学生包括博士生数量全世界最多、人均阅读量全世界最少,网吧爆满、图书馆冷清,与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背道而驰。
大学精神是科学精神而不是鸵鸟精神与阿Q精神
本来改革的目标是消除计划体制下的异化现象,使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教育产业化改革却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更加严重。
高校自主办学以学校利润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学术与超学术的人身依附关系。
高校自主办学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一切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
高等教育应该为我国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做贡献,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GDP增长做贡献。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学校利润与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创新体系要求彻底改变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特别是创造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彻底改变为教育产业化政策服务、把学历摆在学力之上的社会人才体制机制。
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本质。以提高智力为核心,高校教学体制和科研体制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是异化,其结果就是大学生的科学素质低下。不可否认,在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体制机制设计与价值观导向环境中,“读读读,书中自有田螺姑娘”是可能的,“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万两”也是现实的,但“读读读,书中自有原创理论”只是痴心妄想。原创理论不是把“科班”和“科学”画等号的“顶层设计”就能一厢情愿产生,也不是把“民科”和“伪科学”画等号的“顶层设计”就能一手遮天抹杀。面对非科班——“民科”出原创成果的能力优于科班这一客观事实,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唯我独大我行我素行不通,试图靠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假博士整天一只手柱着一根金箍棒一只手对着“民科”竖起中指指着鼻子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喊打喊杀也只能蚂蚁缘槐蚍蜉撼树自欺欺人自取其辱;调适心态调整思路通过正向改革使高校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无缝接轨,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大学精神是科学精神与实事求是,而不是鸵鸟精神与阿Q精神;高校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不是科班而是科学,而科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既不可能关起门来从课堂产生,也不可能通过灌输书本知识得到发展。什么“论”都有、唯独没有“原创论”的“科班论”、“民科论”、“官科论”、“刊物级别论”、“核心期刊论”、“评奖级别论”、“双顶级论”、“影响因子论”、“论文引用率排名论”、“同行评价论”等都是在关门卖学分制度造成我国高校虽占有国家大量科研经费却不但鸟不拉屎而且狗也不拉屎的严酷现实面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南郭先生为南郭先生群体保驾护航的产物,是水货排挤干货、劣币驱逐良币的产物。
这些奇奇怪怪、没有任何科学学根据的所谓学术评价“标准”说明,顶着西方顶级名校博士头衔并不意味着知道原创理论怎么产生;而根本不知道原创理论怎么产生的人,也就根本不知道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怎么衔接。不是从理论本身考察新理论是否真理,而是从一个人的身份、是否科班出身判断新理论是否成立,出于教育产业化目标对高校教学科研体制的顶层设计,使高校教学目标和科研目标完全脱节乃至根本对立。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弱将手下无强兵。没有原创理论、根本不懂原创理论怎么产生的人本来不具备学术评价的话语权;根据高校教学目标和科研目标的内在一致性,不具备学术评价话语权也就不应该具备高校领导权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话语权。执迷于“科班”概念、“国际惯例”和“双顶级”标准的所谓世界顶级名校博士把持我国高校领导权与学术评价话语权,只能培养出一大批高分低能、有博士学位无博士学力的庸才。
“体制弊端”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压抑人的创新能力
“民科”“官科”的学术标准是统一的,“民科”、“官科”的二元区分没有科学根据,“官科”是科学、“民科”是伪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没有科学根据。我国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不是反“民科”而是根本改变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压抑人的创新能力的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
所谓“官科”,狭义指体制内科学家,广义指在自己研究领域取得教育部承认的海内外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人员。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进,“官科”概念有从狭义向广义延伸、广义转化为狭义的趋向。从“官科”的定义及内涵演变可以看出,凡是“官科”的研究成果都是真科学、凡是“民科”的研究成果都是伪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不是基于科学学原理的、规范的、负责任的学术评价,而纯粹是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使学术体制成为教育产业链中一个环节的产物,是教育产业化衍生教育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染指辐射带动学术行政化的产物。
学术行政化,就是在学术资源配置、学术成果评价中,不是体现科学发展规律、促进科学发展,而是体现行政意志、实现行政目标的科研体制。学术行政化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规律,阻碍科学发展。
教育行政化,就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教学成果评价中,不是体现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才成长,而是体现行政意志、实现行政目标的教育体制。教育行政化严重违背人才成长规律,阻碍人才成长。
教育产业化,是把教育由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的改革取向,经过教育产业化改革使教育部门由公益部门转变成盈利部门,在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通过教育产业这个平台纳入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的同时,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为高校带来利润最大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产业化是典型的、彻头彻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垄断的不是一般的自然资源,而是智力资源、社会资源与中国人民的发展权。教育产业化颠倒了学历和学力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扭曲了学术评价标准和社会人才评价体系,破坏了国民创新体系,剥夺了贫穷家庭后代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使GDP、人均GDP指数大大提高的同时,降低了中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实际生活水平,使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感指数大大降低,是改革的异化与社会的后退。教育产业化是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教育产业化的根源。
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民科”话语权
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教育双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伪科学不是民科而是官科,不在体制外而在体制内,而且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只不过因为“官科”掌握学术评价的话语权,有关方面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而刻意掩盖“官科”中的伪科学,放大“民科”中的伪科学。
当体制内——“官科”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官科”的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官科”的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民科”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
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以致造成学术界身份与身价、成就与地位、贡献与待遇的极大反差。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
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的“民科”——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必须让“民科”和“官科”在科研体制、学术评价体系中处于同等地位。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
应该大力扶持民科——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
要在全社会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知识轻智慧、重继承性发展轻创新性发展、重按部就班增长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重持之有据轻言之成理、重引经据典轻自圆其说、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严重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严重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严重异化的人才体制。
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除了彻底改变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外,要打破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人才堡垒,让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人才平等竞争,让体制外—民科的一流科研成果可以畅通无阻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
我国目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以反伪科学为名反民科的浪潮纯粹是贼喊捉贼、李鬼捉李逵的闹剧。这场闹剧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逆流,中华文化发展史的耻辱,是我国学术界的雾霾,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股逆流在中国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必然产物。必须从哲学、科学学的高度对这股逆流迎头痛击以正本清源,还我国科学界以朗朗乾坤,使我国科学得到健康发展。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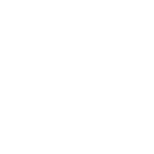


tdsrw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