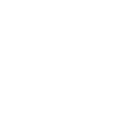苗东升同志是一位好学不倦的学者。笔者几年前从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中心假期研讨会每次结束后,一起和他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就发现他的腿有点行动不便,同行的还有中医师何义英老师,我们都劝他去看看病,他说:他在学校外面的同仁堂药店找坐堂医生看了,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也无大碍,也就不了了之啦。
他每天早6点开始写作,除了午休和晚饭后在校园中散步外,一直研究到10点多才睡觉。除了一年很少几次到校外参加学术活动外,天天如此。长期的固定姿态的写作,身体的机能在不知不觉中每况日下,而天生乐观的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遗传性疾病,再活个十年左右没有问题。
苗东升同志是学数学的出身,大学毕业就投入了国防科技战线,到了钱学森领导的部门工作。实现了钱学森回国时让他作为一个中学生就开始有了要从事航天事业的梦想。他密切关注钱学森的学术动向,除了聆听钱学森在单位的报告外,凡是能够弄到的钱老的论著,他都尽量收集、学习。
虽然近在咫尺,学术上却无请教的机会。苗东升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他参加了钱老主持的“系统科学讨论班”才有了请教学术问题的机会。并将自己结合教学任务写的《系统科学原理》《模糊学导引》送给钱老,并得到了钱老的回复。
苗东升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和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培育下,一直坚持以系统观点看事物,关心世界系统的整体演化,以推动中国的复杂性研究为己任,将钱老的学术思想不断推进。他的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专著就有十几本,论文更是洋洋洒洒近百种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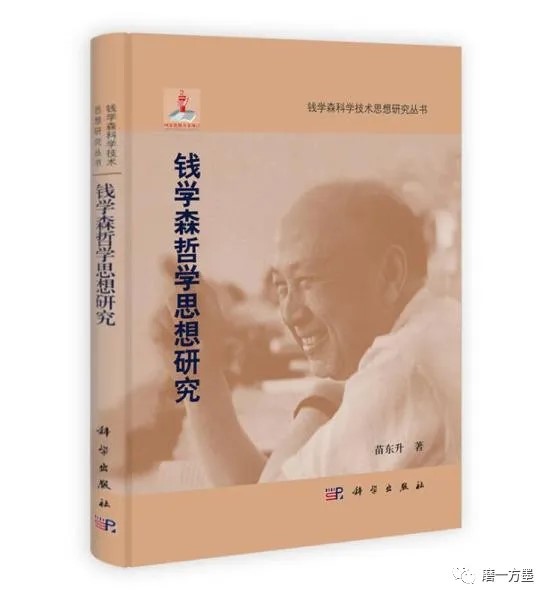
苗东升同志认为:中国的复杂性探索是以世界系统的形成演变为大环境、在世界与中国互动互应中进行的,世界系统的形成、演变改变着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演变也改变着世界。

复杂性科学在西方正式诞生于1970年代,从1956年开始钱学森(下文尊敬地称为“钱老”)为了祖国的强盛,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科技统帅,在1970年代末全身心地回归学术理论研究,重点是系统科学等复杂性研究领域。他首先大力推行对当时世界科技前沿知识的科普工作,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听众讲解系统论等科学知识。笔者就是在听了钱老的报告后,开始关注这一科技新潮的。
钱老的报告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三论”、 用“三论”的热潮。笔者也从此加了魏宏森教授的“‘三论’学习班”开始了扫除自身科盲的过程。钱老自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承续毛泽东的复杂性研究路径,大力推动西方复杂性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同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初创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
毛泽东生前十分看重建立中国学派,在不同场合反复谈论中国要对世界做更大贡献,特别是文化贡献。他的指导思想是:“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把《红楼梦》看成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是第五项发明,用意也在这里。钱老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就是东西方科学文化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的眼睛始终紧盯着中国社会变革,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完全没有注意到西方开始走向显学的复杂性研究。钱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科学技术前沿的新进展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进程联系起来。
毛泽东的矛盾复杂性原理奠定了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哲学基础,以及研究社会变革的方法论;钱老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原理拓展了这条路径的科学基础,把中国的复杂性研究提升到新高度。
钱老赴美留学学的是空气动力学,原本属于典型的还原论科学。但参与美国火箭导弹的早期研制,师从工程学大师冯.卡门,这种实践过程使钱老开始培育避免一味追求简单性的科技理念,让实践经验也起重要作用,而工程智慧是科学理论、工程实践经验和艺术想象力的综合集成。火箭导弹研制看重的是科学新创意。钱老对复杂性的认识最初就萌生于这里。

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疯狂迫害,逼使钱老离开火箭导弹研制,转向理论研究。他的科学观由此而同新兴的复杂性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回国后的钱老远离了西方复杂性研究前沿,浓烈的爱国情怀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到国家最需要他的部门工作。处于开拓中国航天科技的领导岗位,创立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重担,使他获得了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特殊复杂性的实践环境。
他提出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而应用此法“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特别提到建模要抓主要矛盾。谈到这种新科学方法时,钱老曾有这样的表达:不要还原论不行,只要还原论也不行;不要整体论不行,只要整体论也不行。就是说,要把还原论与整体论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把系统论界定为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辨证统一。这是钱老以自己一生科学技术工作的全部经验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故可以视为对矛盾复杂性原理的科学论证。
钱老于1987年最后一天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发表的“惊人之论”,明确把复杂性作为科学前沿的新概念,提炼出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给出系统的一种完备分类,制订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这种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这标志着钱老把建立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他在次年明确宣布:“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复杂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这不是普通的复杂系统,而是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21世纪的世界是整个集体化了的世界”,“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了……这是过渡到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必经阶段。”基于此,提出“世界社会形态培育世界大同”的论断,认定“历史唯物主义要加上这一新篇章”。
从1960年代开始,苗东升就关心世界形势的变化,50年如一日。1980年代起追随钱老搞系统科学,养成凡事自觉以系统思维进行思考的习惯,世界大势的演变就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受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启发,世纪之交曾萌发过一个想法:写一本名为《论世界系统——形成、演变、未来》的书,以系统科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揭示信息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面貌,论证大同世界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追随钱老搞复杂性研究,被他“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言感动,新世纪以来萌发过另一个想法:写一本名为《复杂性科学与社会主义》的书,作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为自己的信仰尽一份力。后来,因为精力和视力转差,只好将这两部书合二为一,写了一部《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尚未出版)与已经出版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复杂性管窥》一起,构成了他研究复杂性科学的三部曲。
大家都熟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它反映了宋代中国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开封这个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而宋代文明成果因为历代皇帝防止“陈桥兵变”重演,而将江山送给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唐宋的文明再没有出现。
苗东升指出基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力量,不论封建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很保守,连祖先的疆域都保留不住,更没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明代郑和下西洋开启了近代史的大航海时代,中国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航海实力。但下西洋被明朝统治集团斥责为“弊政”,停止了航海事业。
随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系统化进程终于让世界系统化进程从此变得不可逆转了。
在世界近代史上,毛泽东第一个从被侵略民族的视角考察世界系统化的完成期,得出结论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将此命题跟《共产党宣言》结合起来,方可更科学地理解世界系统化的完成期,理解世界系统化的不可逆性,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因为只有接受世界已经系统化了这个现实,把中国作为世界系统不可分开的一部分,放在世界系统的整体中考察,才能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是20世纪才能产生的认识。
毛泽东创造的矛盾结构分析方法,非常适用于分析世界系统的结构。
系统科学一开始就关注社会系统,关注系统思想在世界大事中的应用。但把世界和社会合成一个词,形成“世界社会”和“世界社会形态”的概念,可能是钱老的首创。不过,他主要关注的不是世界社会,而是世界社会形态。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到共产主义社会制之间还缺一个大的阶段:前四个社会制都限于一个地区,或限于一个国家,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今天看,这个缺断可以补上了,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已逐渐形成一个大的社会了,哪个国家也不能闭关自守,闭关自守只会落后。”
“21世纪的世界,是整个集体化了的世界”。
“由于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上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世界正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这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
“世界社会也是复杂巨系统”。
世界社会形态是“一个关系到21世纪的大问题”,“首先是树立这个概念,然后再详细论证”。
“今天是世界一体化,我们进入了世界社会形态”。
“在我们面临现代中国第二次社会革命时,全世界已进入世界社会形态。这是客观条件。”
钱老上述新颖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核心课题,颇具理论挖掘的价值。
苗东升认为这些说法的科学性不足。首先应该说,培育大同世界的是世界社会,而不宜说世界社会形态培育世界大同。任何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形态,世界社会一旦形成,也就具有了自己的形态,即世界社会形态。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世界社会依然存在,依然具有它的形态,世界社会形态不会因进入共产主义而消失,只是不同于现在的形态。
苗东升认为直到新中国诞生,我们仍然没有建立起像样的还原论科学,根本谈不上扩展它的应用范围、再超越它而开展复杂性研究。鸦片战争后最初几十年内,中国人只看到自己技术落后,不懂得技术落后根源于科学和文化落后,直到五四运动才觉悟到必须请进赛先生,从科学上赶超西方。但五四精英把科学与简单性科学等同起来,误认为还原论是科学唯一可能的方法论基础,对西方开始孕育的复杂性研究毫无察觉,自然谈不上跟进,却无意中传播了西方科学观中的形而上学。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头30年,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仍然等同于简单性科学,没有注意到西方正在演变为显学的复杂性研究。
救亡图存努力的一败再败,把与西方世界不同的另一种复杂性尖锐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落后根源于制度落后,只有首先变革社会制度,才能真正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复兴目标。中国的复杂性研究必须服务于这一历史总任务,符合这一历史总进程;而第一步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倒三座大山。只有在这里中国的复杂性研究才能获得巨大的历史动力,也只有这里才最具有产生独特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实践基础和时代氛围。这种独特性逼使毛泽东选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复杂性研究路径。
中国的复杂性探索是以世界系统为环境、美国影响日渐增大,亲美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后期甚至左右着中国的政经大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不断膨胀,图谋把中国变为其独家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各种集体运动模式都是围绕如何对待苏、美、日三种外在他组织力量而形成和演变的,复杂性研究的中国路径则是毛泽东在回应这些变化中开拓出来的。
对于大儒梁漱溟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高于封建社会。由此引出毛泽东对他的的批评:“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没有这一认识,毛泽东成不了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开拓者。
他于1946年写道:“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一卷本1156、1158页)命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为其分命题)揭示了复杂性研究的基本信念;用科学学语言讲,此命题是复杂性科学的核心假设,极具理论意义。命题“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则指明应对客观复杂性的正确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切忌简单化,半个世纪后西方有学者称之为复杂性思维。
系统科学是以西方科学技术成就为背景发展起来的,用于分析社会系统尚有许多隔阂;毛泽东的系统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以社会变革为背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而发展起来的,难以直接用来分析科技问题,却是研究社会系统的锐利武器。
苗东升认为在现代世界历史中,毛泽东是第一个从非西方文化氛围中涌现出来的世界历史巨人,他是少数具备了把东西方优秀文化结合起来这种自觉意识和能力的人(马克思和列宁都历史地做不到这一点),更是第一个提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东方人。他亲身参与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作为第一领导人而获得完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最勇敢、最深沉、最全面的思考和探索,其中难免犯错误,但即使错误也是可贵的思想财富。
毛泽东也是打破冷战结构、开创全球化新局面的世界级推手。需要强调的是,列宁未能解决防止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毛泽东却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做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努力,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毛泽东,苏联解体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面临何种悲惨命运,难以设想!这些就是毛泽东对世界历史所发挥的作用,苗东升就首先承认毛泽东是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开拓者。钱老把中国的复杂性研究提升到新高度,并创立了中国学派,其成员主要来自于钱老主持的系统科学研讨班小班,苗东升把中国的复杂性研究的学术成果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现在,我将苗东升的诗句和我的改动呈现于下作为本文的结语:
卡尔润之两昆仑,
西呼东应震苍穹。
砸烂三个从属于,
五洲四海迎大同。
改为:
卡尔润之两昆仑,
综合集成钱学森。
人类命运共同体,
集大成是苗东升。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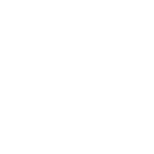


tdsrw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