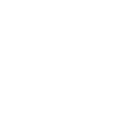宋正海,1938 年生于浙江海宁,1964 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93 年评为研究员,1998 年退休。曾任该所生物学史和地学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所科技史综合研究中心(组)主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正式发表论文和重要文章500 余篇;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等非正式刊物发表文章60 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论文集20 余部;主编丛书3 套。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十多个奖励。先生是一位兴趣广泛且著作等身的知名科技史学家,在地学史、海洋史和黄河学等多个交叉学科领域享有广泛的认可度。先生生性谦和,半生勤勉治学,虽年近八十却坚持科研。因创立且坚持组织和参与“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他本人也面临质疑和争议。不过“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是个群体现象,非常复杂,需要由历史和后世做出科学客观的评断。
张: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很快将迎来六十年所庆,研究所号召年轻人对已经退休的老专家进行口述访谈,丰富我们对老前辈们的治学经验和研究所所史的了解。十分感谢宋老师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您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特别是您个人的性格爱好。
宋:好的。我对研究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很乐意接受这次访谈。我的教育经历很简单。1938 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市)。家中兄弟姐妹10人,弟弟妹妹多人上山下乡,父亲早亡,生活一度十分艰难。我幼年身体较弱,在家门口读了小学,初中在海宁一中就读,1954 年起高中在嘉兴一中,1957 年考入北京大学,家中仅我一人上了大学,算是赶上了时机。初中时,我就对自然科学有着广泛的兴趣,热衷科普图书和杂志,经常与好友一起谈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曾与两位同窗好友李宗岩、咸立金在李家建了一个小小实验室,做些物理、化学等小实验,待黄昏时我们还到空旷地带,对照星图去认识星座。高中时,我离开了家乡,但继续保持着对自然科学课程的热情,十分热爱自然地理学。由于对大自然的感情,当时对《知识就是力量》等刊物上介绍的苏联改造自然的宏伟工程感到很新奇。那时候开始接触自然辩证法并产生兴趣,也集中读了不少小说。但我对语文、历史从没有产生大的兴趣,故成绩一般。
张:大学生活对您今后的人生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有哪些影响呢?
宋:我1957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8-1959年,因病休学一年,又赶上学制由5 年改为6 年,因此我大学一共读了7 年,直到1964 年才毕业获得理科学位。这7年是我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对于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值得回忆。20 世纪50-60 年代,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学科分化和分类研究占主流地位,大学也不例外,但是唯独自然地理学是个例外。因为当时地理学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亟待提出解决办法,在这方面,苏联地理学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强调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四个圈层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自然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联系,有着各个圈层所没有的特性和规律,而自然地理学就是研究这种复杂自然综合体的现状、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
当时,中国地理学就在学习苏联这套综合自然地理学。北京大学自然地理学受到苏联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影响,强调地理圈是综合体,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长期作用形成的。我们当时要学的基础课很多很广,还包括地理学综合理论和基本技术等。在还原论科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大潮中,我能在高水平的大学中学习综合自然地理学,提前几十年打下了多学科基础,接受了正规系统的综合训练,这对于我后来几十年的学术思维和事业开拓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使我在当前科学由还原论到整体论,由简单性探索到复杂性研究的转型中,较敏感地看清科学大潮的变化,并较早为促进“天地生人”的大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做了些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后期致力于从事地球史和地球科学史等整体论科学,但也能从力学、物理、化学等还原论科学来分析问题,并且发表了多篇物理学史、化学史、天体力学史方面的文章。而当时在校内目睹“反右”“大跃进”等经常性的政治运动,也使我经历了大风雨,见了大世面。当时,我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了大自然。尽管后来无缘再跑野外,但与大自然的感情是较深的,这也使我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中蕴含着较强的自然倾向。
北京大学兼收并蓄的学术民主精神的影响使我基本能耐心听取不同学术意见,以提高自己的见解或完善自己的想法。在组织“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后,我能坚持学术平等,坚持多学科交叉和保持不同学术观点间平心静气的交流,有意识支持年轻同志,促进他们的创新。
张:请您回忆一下您当初来到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经历。科技史研究跟您以往的学术兴趣相投吗?
宋:大学毕业时,我分配到我所,此后一直工作到退休。我来自然科学史所工作是很偶然的,可以说是不得已而转行。因对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兴趣浓厚,大学期间我一直憧憬毕业后做个地学工作者,投身大自然,从未想到会以科技史研究为职业。据说,我开始时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生态与地植物室的,但植物所认为我的身体无法胜任野外工作。后来,我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基本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没要我。正在这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所的前身)招收大学毕业生,殷美琴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要人,学校就把我分配到了自然科学史所,说不用跑野外,只做室内工作。殷美琴不敢决定,就回所商量。当时自然科学史所的所领导段伯宇、黄炜均在农村搞“四清”,可能经与当时党支部马约、刘宪宁等同志商量后,同意接收我。我后来多次开玩笑“ 我是作为废品被殷美琴招到我们所的,是废物利用”。
因我对语文、历史没有产生大的兴趣,而对自然科学情有独钟,在不得已从事自然科学史工作后,所涉方面很多,但特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没有重视考证工作,而强调多学科相关研究,努力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科学倾向(优势),致力于整体论发展,强调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等。
张:您对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最初印象如何?是否适应这一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呢?
宋:我1964 年去研究所报到时,我所就已经在朝阳门内大街137 号大院的东北角办公了,这个古建大院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九爷府”(现称孚王府,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图书馆所藏的古籍和旧书不少,但关于现代科学的却少得可怜。由于当时全所大部分人在通县(今通州区)和安徽寿县搞“四清”,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留守的研究人员基本属于“老弱病残”。我们这批1964 年的毕业生正赶上跟所里老同志到安徽寿县一起“四清”,所里照顾我让我回京。当时共有钱宝琮、王奎克、汪子春、吴和梅和我五人,大家都集中在西厢房一个有套间的外间办公室。
物理学家叶企孙每周会有两天来到研究室,指导天文学史和物理学史的研究。这个环境很安逸,大家都彼此和气,但我仍一度很不习惯。因为刚脱离了生气勃勃的大学生活的我,对于今后藏身在这人少而冷清的古建筑中埋头读古书,从事发掘遗产工作并没有思想准备。当时,也远远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科学史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价值。
张:那您后来是如何从一名外行成为科技史研究的专家?有老先生提供指导吗?
宋:分配到研究所后,我才知道自然科学史所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机构。这虽不是我向往的现代科技和大自然探索,但深信国家成立此所必有重要用处。我身体不好,研究所还同意我来所工作,充分体现了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所以我没有任何专业偏颇。当我了解到,竺可桢最初创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目的是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以驳斥当时国际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我就爱上了科学史。
我所老先生和其他科学史研究者对青年人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们大多很善良,为人正派,是我们年轻人学习做人的榜样。关于业务,当时全国尚没有专门培养科学史的系或专业,我们新来所的大学生要搞科学史研究,均要补学许多知识。所内专门安排古文献课等课程,但更主要在实际工作中由老同志带着搞,边搞边教边学。我所老同志实际上以老师的身份,热情帮助向他们请教的年轻人,我也是如此。虽“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因派性影响了团结,但“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派性的消除,又逐步恢复相互关心和帮助。年轻人之间相互帮助和关心,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张:您印象比较深的老领导和老同事都有谁?
宋:我分配来到自然科学史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段伯宇同志。他哲学水平很高,虽然是高级干部,却平易近人。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他有关我身体健康的金玉良言,并心存感激。我年轻时就体弱多病,大学曾休学一年,毕业分配时,北京植物所、北京地理所因我无法胜任野外工作而拒接纳,感谢我所最后接纳了我。来所后我又因身体不好而从“四清”工作上回北京,故一度很悲观。有一次,在与段伯宇同志聊天时,他知道我情绪很不好,就给我打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水罐,一个有些破但可以用,只要每次用时很小心就可以用很长时间。另一个水罐是好的结实的,但正是结实的,所以人们用时往往就不小心,这样可能一不小心就碰碎了不能用了。他的话让我很受触动,自此我改变精神状态,生活中特别注意身体保护和锻炼,身体慢慢好了起来,现在年近八十仍能继续工作。
张:叶企孙每周两次去研究室,那您跟他有具体的交往吗?
宋:叶企孙先生并非是我所编制。他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又在我所兼任研究员,所以每星期一、五来所。大约有一年时间,我有幸与叶企孙先生在同一办公室。他来所不去别处,一头就扎在我们办公室套间里。
可惜其时政治斗争空气还很重,大家也很小心。我所同志尽管对叶先生很尊重很客气但见面只打个招呼,交谈很少,我们也只能这样。叶先生也同样,见面只点头示意很少说话并很快进了套间里间。除了倒开水,基本不见出来。他背有点驼,坐下来就是看书。书是大厚本的旧的外文书。就这样一坐就是一个上午。尽管里外间没有门相隔,但我们外屋的人也不会进去,他也不会出来进行交流。当时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学识很深,知识广博,值得尊敬。
当时我所人不多,所以吃饭就在科学出版社食堂。通常我们吃饭时叶先生还在看书,较晚才回家。一次,我较晚去出版社食堂,叶先生突然出来对我说,小宋,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他。但当他后来说是到大同酒家(在王府井北口华侨饭店下面),我突然有点慌张,忙说不去不去就跑了。后来我回想此事,感到很内疚,辜负了叶先生的好意。后来“文化大革命”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最早开始,学部大乱,我所也是两派。叶企孙也不再到我所看书,我也不再见到他也没有打听他的消息。后来1975 年,我与我所邢润川同志合作撰写《万有引力定律究竟是怎样发现的?》一文,就是否能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找叶先生把关。
作者简介
张志会(1982-),河北省保定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水利史。
宋正海(1938-),浙江省海宁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地学、海洋史和黄河学。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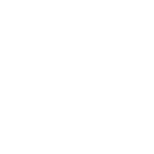


tdsrw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