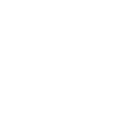妙手回春
我们每个人都与中医有“瓜葛”。
眼下的“90后”“00后”,显然很在乎那些情人节、圣诞节,但他们也不会忘记板蓝根。但凡幼时“上火”,或是如今喜欢吃烧烤,长辈总会令他们吃几片板蓝根化解,以免嗓子发炎,酿成病症。而往上数几代人,大都有被中医救治的经历。
我是感恩中医的,中医曾救活弱小无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块“妙手回春”的匾额,今生是挂在我的心里了。
我父母自由恋爱结合,喜得爱女,然不到一岁,婴儿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后来我看史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非到疑难重症时,才进这家医院不可”的,因为它收费高昂,床位不易得。而濒临死亡的我,却被甘美医院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作者“百日”时与父母合影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家里“叮咣”响着木匠作业的声音,里屋躺着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如果不是到了无门可投的地步,我父母是不会让一个路人来医治爱女的。游走四方的“草医”,是连门诊铺面也没有的,正如此次在武汉参与抗疫的“游医”。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潦倒、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边的黄公东街富滇银行宿舍,一幢气派的法式洋楼前,挺有底气地“喊了一嗓子”,而后拘谨地走进我家,到小床前看这垂危婴儿,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还以为“完了”,仔细一看,是宁静了。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父亲拎起小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视为至尊的几位先驱,胡适、鲁迅,都排斥中医。究其原因,有因个人的经历而怀有厌恨的,也有因改革“旧文化”的意愿太迫切所致。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
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在现代史上,中医身影飘零。在教科书里,大概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为政”,而非“医理”。
当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荣获诺奖,中医中药才在世界上喊响了“这一嗓子”。可惜,在医学界不见太大的反响。屠呦呦说,祖国医学里还有许多珍宝值得后人发掘。
我插队的德宏,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吃过“瘴疠之气”的大亏。唐代天宝年间征讨云南,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里反复提起的也是瘟疫:“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对瘟疫的恐惧,使当年这位壮丁自折其臂。直到从金鸡纳树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宁,对疟疾才有了控制。我这个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疟员”,每天收工后把药片送到傣家饭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还没有唱响全国时,我参加下乡医疗队到滇南石屏县,趁机学习中医,不辞做最辛苦的事情:上山采药,回来晾晒、焙治,管理药房。我对“脉象”把握精准,得到队里中医的赏识。“洪脉”“滑脉”“弦脉”都与文学的意象相通,所以学中医是必须学好中文的。“把脉”是中医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说不准病情的。我把脉时还发现了两位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出实情,若不调整处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四气五味,八纲辨证,中医原理与中国人日常说的一些成语是沟通的,如“阴盛阳衰”“此消彼长”“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不会高过自然,人要配合、服从自然。例如四季的饮食与作息,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也是万物的规律。这些思想不断深化,影响着我的人生。
假如不是高考恢复,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医。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也没有消毒的东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张曼菱采访李政道
2015年春,我到台湾世新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我将一批云南白药产品分送给台北的西南联大学长。抗战时期,云南白药支援前线,深受将士们的喜爱,也在这批“高知”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
我到“金三角”探望远征军眷村时,看到东南亚人民和华人依然崇奉着中医,将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至宝。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里,开设有中医课程。
然而在我们这里,中医院校与一般高等院校相比,总有种入“另册”的感觉。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到云南中医学院讲学,院长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多为贫苦学生、农民子弟,且多数是女生。
中医顽强地生存着,“清贫”是它的特征,也是它与人民不可断的纽带。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将中药视为家常必备之物。谁家抽屉里不会收着几盒廉价的中成药呢,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谓功德无量。因为朴素,因为可靠,反而被轻视,这很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对待亲人的态度。多年来,我们不就是这样对待中医的吗?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退缩到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高于西医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医与这个民族是同生共死的。在那些著名中医的传记里,总有这样的故事:当无名瘟疫暴发,中医临危受命——这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灶架锅,熬药施救。民众们端碗喝药,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制的不同药方。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救人救疫,岂论成败功过,只谓问心无愧。
自“神农尝百草”到我们那些历历可数的家珍——《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历千年护佑着这个民族。世界上,瘟疫与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渐渐被荒漠湮没,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地方。
西医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没有胜算不会出手,它是一门科技,能够发出“科学的判断”。也正是这一点让现代人质疑中医。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相比,中医只有“望闻问切”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说法。这是中医的“短板”,“得手”与“失手”都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因而发展很慢。
至于“庸医”,其实每个行当中都有优劣之分,但西医因为有诊断的科技凭证,“误判”往往能够得到开脱,而世人对中医则“人死必究”,故“劣迹”斑斑。
“疫”火重生
去年,我通览一本《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学者皮国立著),主轴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中医与西医在细菌学上的不同医理和对抗,可谓艰涩探索。其视角是中西医的“对决”,作者对中医怀有危机感,甚为悲观:
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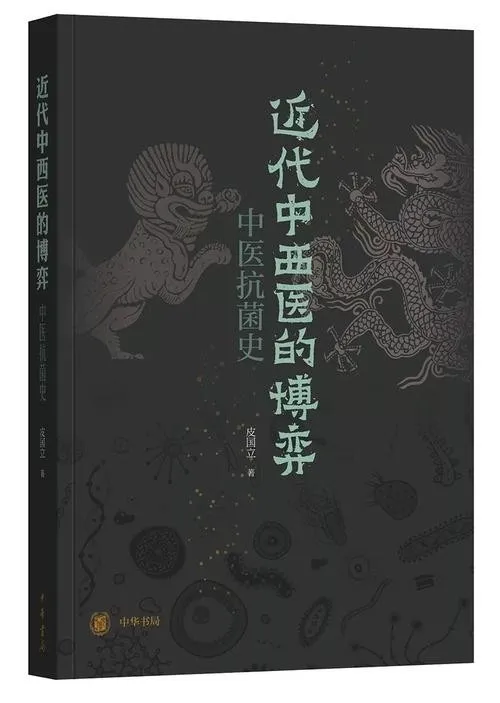
我想,隔着海峡,皮国立先生一定也在关注大陆的抗疫之战。他会惊讶并欣喜地看见,在中国大陆这块母土上,所谓“没有硝烟的战役”,再也不是中医和西医的“对决”,而是二者携手同战病毒——医生们没有执着于学理上的分辨,没有门户的私心,完全从救人的实效出发,互相印证,各得其所,各出妙招,共同制定方案。
引用武汉抗疫前线一位西医的话:“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
就在前几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中谈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轻度症状,能够自愈或治愈,并不会发展为重症。”轻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排毒”过程。如果没有中医的介入,“自愈”对于很多基础体质不好的人,是很难实现的——病毒损坏了人的生理机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联合对抗疫情,才构成了“自愈”的安全轨道。没有中医,轻症患者的占比恐怕不会是80%。

2月14日,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武汉江夏区方舱医院开始收治患者
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学,中医正在成为开放的医学,吸纳西医的诸多手段,补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诊断标准。而西医也乐于“就地取材”,与中医握手言欢,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西医”。疫情中的医者,也是仁者与智者,正在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观。
近年来,中医课程进入了小学课堂——作为中华民族“大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没有理由不进入。我想,这并非让孩子背“汤头”,而是要让他们懂得“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多读一些历史上中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懂得医德、仁爱,让他们学习中国传统道家的哲学,如《道德经》,因为它和中医是一体的。学中医,就是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来的。不仅是小学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天人合一”“万物渐进”的道理,懂得“无为而治”会使身体和社会都安静下来,少一些破坏性的骚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本是中医的医理,也可成为疫情中的我们自强不息、正气凛然的座右铭。
闯过这次大疫后,我们更应该为子孙万代栽培好中医这棵庇荫大树,留下防护堤,中医不能再疲软下去了。都想一想,为中医的发展还能做些什么吧。
(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20年2月28日15版)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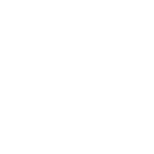


tdsrw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