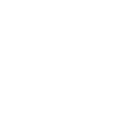吴国盛,男,湖北广济(武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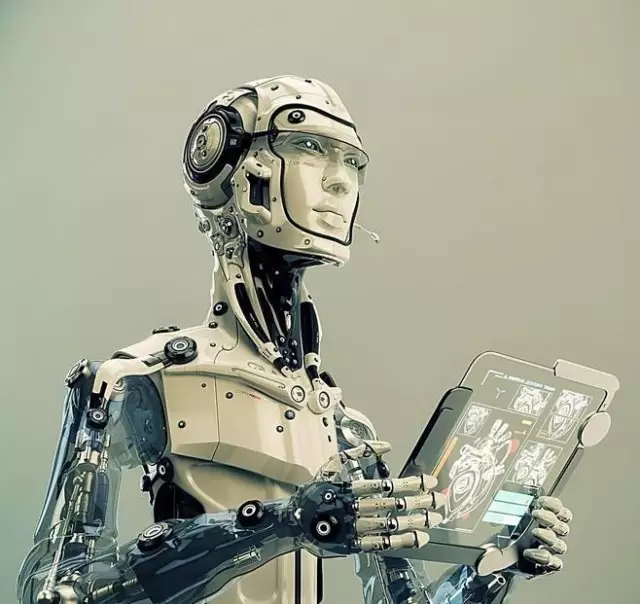
“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尼采的说法,是对现代人,或者承载着现代性的人类的一种刻画。在尼采看来,现代人的本质在于总是渴望实现自己、渴望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这种渴望就是意志。这种意志追求实现自我、掌控世界、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它必定要采取实验的方法,以掌控自然、改造自然为目标。人类自直立行走以来,就一直不自觉地以一种微弱的力量、缓慢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然而现代科学自觉地、主动地,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专事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这是极其不寻常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现象。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智力水平不够,也不是不希望过上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而是缺乏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是在基督教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如果说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science for truth),那么现代科学就是求力的科学(science for power)。它们的区别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地位的改变。对希腊人而言,自然是内在性的领域,是理性和真理的处所。人只能认识自然、追随自然、模仿自然,而不可能改造自然、制造自然。基督教把理性自由改造成意志自由,创世观念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唯名论运动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强化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弱化了形式因、突出了作用因,炼金术、魔法为改造自然作出了示范。于是,人类征服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
从理性自由到意志自由
我们在前面讲过,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是西方人与传统中国人的根本分歧,正是自由的人性理想,造就了科学这种希腊人特有的人文形式。因此,我们现在追究现代科学与希腊科学的区别,也应该把眼光首先对准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与现代自由观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说认识到理念的逻辑(并且自觉遵循这种逻辑——按照希腊人这是必然的)就是自由,没有认识到就是不自由。换句话说,你有知识,你就是自由的,你没有知识,就是不自由的。没有人故意犯错误,犯错误都是无知造成的,因此苏格拉底说无知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缺陷。这个命题到黑格尔这里讲得最为清楚——黑格尔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对希腊人来说,追求自由就是追求自知,就是认识你自己。西方的知识论、认识论始终占居哲学的核心地位,这和希腊人的自由观有关系。因为自由就是服从理性,就是服从内在逻辑、服从必然性,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自由。
基督教对自由概念有新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意志自由。正如阿伦特所说,希腊人不曾有过意志概念,意志问题是基督教引入的新问题。
所谓意志,是人的一种自主的选择能力。意志自由指的是,你本可以不做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因为有意志自由,人们对于自己所做事情就有责任,因为你之所作所为是基于你自己的自由选择。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基于你的自主选择,那你就无责任可言。你做了好事,不值得赞扬;做了坏事,也不必谴责。一个精神病杀了人,用不着被处以极刑。一个明知有危险,仍然冒险救人的人,才真显出其道德的光辉。因此,一切行善和作恶都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没有意志自由,善恶无意义,道德无根据。
意志问题的出现与基督教本身的基本教义相关联。基督教面对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责难是,上帝既然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善者,为何他创造的世界上充满了不幸、罪恶和灾难?为什么他不创造一个全善的世界,让人类或者至少他的选民享受纯粹的快乐、免于遭受不幸和灾难?护教神学家们对此有经典的解释。他们说这一切都不是上帝不全能造成的,而是人类自由所造成的,是人的意志自由所造成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本来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可是他们偏偏选择了一个上帝不让他做的事情,这就使全人类拥有了原罪。原罪的根源就在于人是自由的。上帝的确知道并且能够阻止人类犯罪,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也要人有自由。不仅好人是自由的,坏人也是自由的。你要想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恶,除非消灭掉人的自由意志。但消灭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无所谓善和恶了。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自由的,而作为上帝的最高造物的人也分享了上帝的这一品性。这种分享的代价就是,人要经受苦难、成为戴罪之身。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教义之中一以贯之的逻辑是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没有这个意志自由,许多教义就讲不通。基督教强调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所以正统教会坚决否定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宿命论。
希腊人想当然的认为,人发现了理念的逻辑就必定会追随这种逻辑,但基督教却发现,人的意志自由恰恰就在于,他有能力不服从理性的逻辑。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你就是有能力不照着对的去做。也就是说,你有非理性的自由,有愚昧的自由,有无知的自由,有犯错误的自由。当然,反过来,你也有理性行为的自由、有行善积德的自由、有不犯错误的自由。
这种意志自由的维度,对于理解现代性是非常基本、非常必要的。现代人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情,“我要……”成为现代性生活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前现代时期,人们通常说“我服从……”:我服从道理,我服从上帝的旨意,我服从传统等等。但从现代开始,人类生活的主题就不是“服从”,而是“要”(will)。这种主体意志概念的确立,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框架。
新时代的人不光要推理、论证、演绎,还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要有欲有求,而且要通过推理、论证和演绎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对于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对于现代人来说,他的最高贵的姿势恐怕是做一个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闯天下,要有所作为。你可以做勇士去格斗杀人,也可以做演员去做秀,总而言之,你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你个人的方式实现出来。要做事情,不要闲着。闲着是最大的反人性。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个经典的段落,差不多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宣言。保尔说,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在他临终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一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这个思想表达的是现代新的人生态度,那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意志”得以实现。尼采把现代性的这一核心部分归结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也可译作求力意志。对西方人而言,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希腊时代,认识到理念的逻辑就是实现了自由,而今天,实现自己的意志,才是实现了自由。“求力意志”成为新时代的人文标准。
人类中心主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成了一个问题。主要因为地球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早期开始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出现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希腊人并不认为人是最高的东西。有个别希腊思想家如普罗泰哥拉曾经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但这个思想并不是从存在论上将人确认为万物的中心,而只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并且很快被追求知识确定性的希腊思想主流给否定和抛弃了。事实上,整个希腊主流思想都认为,神才是最高的,而人不是。诸神的世界决定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人只有通过认识神界的意义才能获取自己生命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学就称为神学。
基督教的创世思想一下子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地位对比。首先是自然的地位被大大降低,其次是人的地位被大大提高。我们先讲人的问题。
按照创世思想,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被上帝创造的,因而在根本意义上丧失了神性。原始文化中形形色色的万物有灵论、物活论、多神论统统被扫荡。然而,在众多受造者之中,人享有最高的地位。他是上帝按照自己的面容来创造的,因而具有神性。上帝在用泥土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后,朝亚当鼻子里吹了一口灵气,使亚当成为一个有灵魂者。人类因其灵性,而成为万物之灵长。接着,上帝赋予人治理地界事物,管理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走兽的权力。在圣经中,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是由人类始祖亚当命名的。这样一来,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上帝在世间的一个代理者、一个管理者,一个分享了有限神性的存在者。宇宙万物仿佛是为了人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人的拯救而搭建的一个舞台。无论如何,上帝之下,人是最高者,人分有神性。
基督教虽然为人类中心主义打下了基础,但仅凭创世思想并不能直接导出人类中心主义。毕竟对于基督教正统教义来说,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与唯名论运动直接相关。
前面已经说过,唯名论运动创造的上帝唯意志的全能形象,使得这个世界碎片化、充满了不确定,人生的意义变得难以把捉。虽然后果严重,但它的逻辑却相当坚硬,暴露了基督教教义中内在蕴涵着的隐蔽的逻辑,因此引发了基督教思想世界的强地震。唯名论运动就像引爆了基督教世界内部孕育出的一颗超级炸弹,把这个世界炸得粉碎,而人文主义是从唯名论运动所造就的废墟之中生长出来的替代品。
德国思想史家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最早认识到唯名论运动在现代欧洲的革命性意义。在其《现代的正当性》(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一书中,他提出,唯名论运动是基督教诺斯替主义的第二次复活,即把上帝看成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全能意志,从而摧毁了经院哲学家们营造的理性而温情的上帝形象。然而,唯名论运动把世界搞成了一团偶然性、不确定性,使“得救”的希望变得渺茫,从而使基督教思想世界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布鲁门贝格认为,正是为了克服这个严重的危机,现代性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现代性的基本克服方案是,让人挺身而出,“成为像上帝那样”,着手挽救这个混乱、无序、令人绝望的世界。
“唯名论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对神的看法,而且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对人的看法,它比以前更强调人的意志的重要性。”[1] 唯名论者强调,人是上帝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分享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人之为人更多的在于它的意志而不是它的理性。尽管唯名论关于意志自由的人的形象不可能在神学中贯彻到底,但为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所继承。
以彼特拉克为首的中世纪晚期人文主义者继承了唯名论的“个人主义”传统,但把人的意志由一种单纯的被创造的意志转化为自我创造的意志,也就是分享了唯名论者赋与上帝的那种创造的意志。“人文主义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来回答由神的全能引出的问题:设想一种新人,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唯名论所设定的混乱世界中保护自己。”[2]
人文主义者强调人是以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的,试图让人分享上帝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通过对人自身的认识,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因此,通达上帝的道路必定要通过人这个环节。这样,他们就把人逐渐确立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显著的路标是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笛卡尔以他的“我思故我在”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新纪元。为什么这个口号这么重要?笛卡尔要为知识的确定性寻找一个基础,这本身就是直面唯名论运动的恶劣后果,从混乱、无序、碎片化的世界中拯救知识从而拯救世界的伟大尝试。笛卡尔认为,一切事物都应放在“普遍怀疑”的探照灯下进行考究,绝不轻易认同一项事物为真,直到能够找到绝对无可怀疑的事物为止。结果,他真的发现了“我怀疑”这件事情是不能再怀疑了,而这个怀疑的动作就是“我思”。从“我思”的无可质疑中,可以解析出“我(在)”的无可质疑。这样,就导出了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
这里的“我”自然不是笛卡尔本人,而是任何一个思维着的主体,因而是大写的人。从“我”出发构造一切哲学、一切知识,让“我”成为出发点,这当然是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里,笛卡尔丝毫用不着上帝。既不用上帝作为知识可能性的保障,也不怕唯名论的上帝破坏知识的确定性。他在上帝之外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像上帝一样,自我确定自我、自我奠基。这个抽象的主体,没有时间性、没有人格,因而不受制于这个世界的有限性,反而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主人。它的意志与上帝一样是无限的,因此它能够把一切事物构造为自己的表象,而自己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体。“思想”是一种意志,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将“被思者”构造为表象。“构造”行为成为人的意志行为。现代人正是从这种“我思”出发,获得了与上帝一样的创造性能力。人与上帝的区别只在于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渐进取得的,除此而外,它几乎就是上帝。
与笛卡尔同样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之奠基者的弗兰西斯·培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笛卡尔一样,培根也深受唯名论的影响。他在《新工具》中说:“在自然当中固然实在只有一个一个的物体,依照固定的法则作着个别的单独活动,此外便一无所有,可是在哲学中,正是这个法则自身以及对于它的查究、发现和解释就成为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动作的基础。”[3] 这表明培根认同唯名论的基本观点。与笛卡尔不同的是,培根并不认为人类个体有多么伟大,但他认为人类群体,特别是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可以构成一个持久的人类意志。他没有笛卡尔那么宏大的气魄和野心,没有把人立为超越的上帝一般的主体,但还是坚定地认为人是世间万物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他在《古代的智慧:普罗米修斯》中说:“如果我们考虑终极因的话,人可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类,剩下的一切将茫然无措,既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如寓言所说,象是没有捆绑的帚把,会导向虚无。因为整个世界一起为人服务;没有任何东西人不能拿来使用并结出果实。星星的演变和运行可以为他划分四季、分配世界的春夏秋冬。中层天空的现象给他提供天气预报。风吹动他的船,推动他的磨和机器。各种动物和植物创造出来是为了给他提供住所、衣服、食物或药品的,或是减轻他的劳动,或是给他快乐和舒适;万事万物似乎都为人做人事,而不是为它们自己做事。”这段话明确显示出,培根以人为万物存在的目的。这可以看成是另一个版本的略有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
以笛卡尔和培根的哲学为形而上学基础的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人的科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
征服自然
笛卡尔版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有着无限的意志,而这个无限的意志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的无限征服和掌控之上。通过对自然的掌控,主体性完成对自身的确立。
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自然物是那些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比自身不拥有运动源泉的制作物高出一筹。制作物的最高成就也就是模仿自然,因此,包括艺术、技术在内的制作性的知识在知识谱系中的地位,远远低于物理学(自然学)这样的纯粹理论知识。人工巧夺天工是不可能的。认识自然必须以一种沉思的态度,即纯粹静观的态度,从认识自然的范畴开始。任何试图干预自然过程的行为,都会影响对自然的认识,得不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希腊古典科学没有发展出实验方法,不是因为技术水平有限,而是因为希腊知识论背后的存在论所致。这种存在论预设了,实验对于物理学不仅是不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创世观念大大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作为受造者,原则上就分享了偶然性,而丧失了自主性。但是另一方面,自然既然是上帝的造物,而且上帝看着是好的,因此地位也并没有很大的下降。经院哲学将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义相结合,把自然界重新按照共相结成一条合乎理性的存在之链,仍然维护了作为理性体系的自然。真正让自然身份大大贬低的是唯名论。
唯名论极端强调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意志、全能和任性,拒绝共相真实的起作用,使自然物彻底丧失自主性和内在根据。原本用来解释自然物之所作所为、使自然界结成一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被否定。唯名论实际上使自然裂成碎片。每一个自然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直接接受造物主的支配,并不存在某种自然物“必定”遵循的坚不可摧的内在逻辑。对于这样的自然界,认识如何可能呢?
作为对唯名论危机之克服的现代性以及现代科学,虽然为了解决唯名论造就的不可解决的困难必须另起炉灶,但实际上继承了唯名论的思想遗产。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从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自然哲学(物理学)中摆脱出来,重建一个以动力因为主要因果模式的自然知识体系,借助的就是唯名论革命。
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认识一个自然物,需要认识它之所以为它的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动力因。四种原因,缺一不可。以一个制作物为例,可以很好的解释四因。比如皇冠,其质料因是黄金,形式因是它的形状,目的因是皇家举行盛典,动力因则是工匠。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四因俱全,我们才能说真正理解了这件事物的本质。自然物与制作物不同,它的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都在自己的内部,因而可以合三为一。一粒麦种的形式因是麦子,目的因是成为麦子,动力因也是成为麦子。麦子的理念或者共相或者种相或者形式,就是麦种长成为麦子的动力。在麦种长成为麦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事物出现,只不过是潜能转化为现实。麦子是现实,而麦种是潜能。因此,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及其所代表的希腊思想主流而言,头等重要的是范畴(Category)、共相(Ideal)、形式(Form)。一旦确立了某件事物的共相,这件事情的内在逻辑就开始起作用。知识本质上通过演绎推理被展现出来。亚里士多德的整个物理学,包括四元素说、四因说、自然位置与自然运动、月上月下的宇宙论等,都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经院自然哲学全盘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只是把共相看成是上帝的理性。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为所有的事物提供了一整套形式因。
唯名论破除了共相的实在性,不承认上帝为所有事物提供形式因的说法。如果上帝提供了形式因的话,事物就会自行其事,连上帝都奈何不得。这令唯名论的全能而且绝对自由的上帝无所适从。唯名论强调,上帝可以随意变更任何事物的样貌和本质,因此,变化乃是自然界最重要、最值得重视的事情。上帝的意志就体现在自然的运动上,或者说,自然就是上帝的意志运动。与经院哲学不同,唯名论的上帝的意志不是万物的形式因,而是它们的动力因;不决定它们的本质,而决定它们的未来。作为自然界知识体系的物理学,必须关注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之中存在着的法则。这是唯名论给现代自然概念带来的最革命性的变化。
笛卡尔版本的人类中心主义让人拥有如上帝一样无限的意志,而这个意志首先是指向自然的意志。在笛卡尔看来,上帝的意志就是它的理智,就是自然界中的因果性,而人的意志是思想。思想的基本功能是创造对世界的表象,因此“我思”自我肯定,把自我确定为世界表象的主体。正如上帝的无限意志支配着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人的无限意志则是认识从而掌控自然。掌控的方法是,把自然界表象成一个数学的体系,把经验之流通过直观转变成物体在数学空间中的运动。借助普遍数学,人类的意志认识并且掌控了这个数学化的自然。
正如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培根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对人类知识不能转化为实际力量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希腊人都是小孩,光知道娱乐、玩耍,大好的智力都用在不切实际的纯粹理论方面,很可惜。希腊学术都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对话”[4] 应该让知识为人类造福,因为人类的知识就是人类的力量。“人类在一堕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在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5] 培根大声疾呼,“让人类恢复其统治自然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神慷慨赐予人的。”[6]
在培根看来,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这是为现代科学定下的一个基本目标。希腊人认识自然并不是为了改造自然,认识本身就是目的。但培根眼里的科学大不一样,必须把改造自然作为目的,而认识只是手段。正是这种新哲学,使得现代科学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纯粹科学,而是一开始就包含着实际运用的内在可能性。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原因即出于此。我们中国人的确比较容易理解科学与技术这种密切的关联,而且一向科、技不分,我们缺乏理解的只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那样密不可分。
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个有用之学,原因就是,它奠定在人类和自然的一种暂新的关系之上。由于自由的理念发生改变,由理性自由转化为意志自由,人与自然之间单纯的认知关系转化成掌控、操作关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概念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本前提。
实验科学
征服自然的理想最终落实到实验科学身上。
所谓实验科学,是指通过人为设置的特殊条件对自然过程进行干预,从而发现自然物发生变化的规律。实验科学大行其道,首先必须填平自然物与制作物之间的鸿沟,打破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的界限,建立自然可以被(人类)制造的观念。
自然观念上的这种突破也有其希腊根源。柏拉图最先质疑自然与技艺的二分。他在《法律篇》中总结说,从前的哲学家们认为日月星辰、天地万物均出自自然,是自己生长的结果,而技艺是人类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而且只是对自然的模仿;有些技艺是与自然相协调的,如医学、农耕和体育,还有些技艺协调得差一些,如政治,而立法,则协调得最差。[7] 但是,柏拉图本人并不赞成这种观念。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一个自足自律的过程,同样也是被创造的,也是技艺的产物。他在《智者篇》中写道:“所谓自然生成的东西,其实是神工所为;只有人从这些东西中制造出来的,才算是人工所为。因此,制作和生产有两种,一种是人的,一种是神的。”[8] 也就是说,就其作为制作而言,自然物和人工物是一样的,区分只在于作者不同。但是,柏拉图的这些思想最后被亚里士多德所掩盖和取代。
最先打破自然物与人工物之分野的,不是哲学家、理论家,而是炼金术士这样的实践家。炼金术传统起源于埃及,目标是通过锻烧、熔合等方式将铜、锡、铅、铁这样的贱金属转变为黄金和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从今天的眼光看,炼金术的目标即通过化学方式使元素嬗变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个绵延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传统既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技术,也有它的哲学根据。他们相信,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只是这种改变在自然状态下发生得比较缓慢,通过人为干预可以加快这种改变的速度。
希腊哲学为炼金术提供了部分理论根据。柏拉图在其《蒂迈欧篇》中提出,物质质料本身是没有任何性质的,之所以能够显现出不同的物质性质,是因为被注入了形式,而这些形式是可以相互嬗变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自然哲学则认为,万物都内在的向着自己的完善状态努力,把一种处在潜能状态的自己实现为现实的自己。希腊晚期的斯多亚派哲学家进一步强调,自然界中一切物体包括金属,都是活的有机体,它们在内在精气(普纽玛)的带动下,都有向更完美状态生长的趋势。这些思想被综合成炼金术的基本指导思想:一切金属都有朝着黄金嬗变的自然趋势,炼金术的工作就是使这一趋势加速。
公元1-5世纪的亚历山大城造就了炼金术的第一次兴盛。这是希腊哲学与埃及神庙手工技艺相结合的产物。埃及炼金术士发展了表观处理技术、合金制造技术,通过对金属进行焙烧、熔化,再进行合成、着色等工艺,使金属合金着上白色或黄色。于是,他们就认为得到了成色十足的白银黄金。在这一炼金的过程中,他们制造了许多玻璃器皿、陶瓷容器,发展了蒸馏、升华、过滤、加热、保温等技术,发现了金属化学反映过程中的不同变色现象。
阿拉伯人掀起了炼金术的第二次高潮。阿拉伯炼金家认为,所有的金属都由硫和汞这两种基本的物质按一定的比例复合而成。硫具有易燃性,汞具有可塑性和可熔性。硫不够会产生银,硫过多会产生铁或铜(易燃、坚硬和难熔),过多的汞会产生锡或铅(柔软易熔)。只有在合适的比例搭配下,才会产生黄金。元素嬗变不过是改变这两个基本元素物质的比例。阿拉伯炼金术引入了物质组分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更接近现代化学。
阿拉伯炼金术在中世纪大翻译运动中连同希腊哲学著作一同传入欧洲。早期经院哲学家对炼金术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元素嬗变的概念以及阿拉伯人的硫-汞金属组分理论持赞同态度,但都主张这种嬗变只能在自然界中存在,对炼金术士的实践是否能够真的实现这种嬗变持怀疑态度。罗吉尔·培根喜好炼金术,而且亲自实践操作,认为经过炼金家加工出来的灵丹比天然黄金有着更为均衡的元素比例。由于炼金术部分禀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部分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有时能够得到基督教世界的容忍,在民间作为秘术流传。但是,炼金术士认为自己可以加速自然过程,甚至改变自然物的种属,这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直接矛盾,因而不为多数经院学者所认同。教会有时候也打击炼金术士,认为他们是一伙骗子和金银的伪造者。但是,炼金术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人类实践活动,体现了人类参与自然过程、控制自然后果的强烈意图。
中世纪晚期,炼金术士也创建了独特的自然哲学以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相抗衡。最近的科学史研究表明,13世纪形成的微粒炼金术(Corpuscular Alchemy)为现代机械自然观、原子物质观以及实验科学开辟了道路。13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塔兰托的保罗(Paul of Taranto)在其托名格伯(Pseudo-Geber)出版的《完满大全》(Summa perfectionis magisterii)中,用微粒论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实体理论。按照亚里士多德,一个自然物之所以如其所是,是因为形式因在起作用,这个形式因构成了这个自然物的质的规定性,并且这个质的规定性是最基本的,优先地支配着其余的规定性。微粒炼金术则认为,自然物的同质性首先在于作为构成组分之微粒的同质,而非预先存在的形式。微粒的聚合和分解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炼金术等手工艺制作业受到基督教欧洲知识界的接纳,与基督教世界对手工劳动的态度有关。在希腊古典时代,手工劳动专属奴隶,因此地位低劣,而且工艺主要关注感觉而不是理性,因此在知识论上的地位也很低。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粹知识,包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数学;第二类是实践知识,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第三类是制作的知识,包括技术、诗歌、绘画等。手工艺无法为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做出什么贡献,因而受到贬低。基督教一方面把手工劳动看成是人堕落之后世俗生活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又把体力劳动看成是人类赎罪忏悔的一种必要方式,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劳动持部分肯定的态度。“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是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发展,以及手工业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也改变了人们对手工业的传统态度。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法术、炼金术、占星术、神秘教义一时兴盛,被称做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著作《赫尔墨斯文集》大为流行。这位赫尔墨斯被认为是与基督教先知摩西同时代的古埃及圣贤,同样受到上帝的启示,其著作因而代表了神启的另一个秘密来源。他因为精通炼金术、占星术和通神术这三种宇宙智慧而被称为三重伟大。赫尔墨斯主义认为人类是“小上帝”,可以通过自然法术来改变自然和控制自然,这一点与人文主义运动的主旨不谋而合,因而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极大欢迎。由人文主义者推波助澜从而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赫尔墨斯主义,极大的促进了实验科学精神在现代早期的生长。以赫尔墨斯主义为旗帜,人们希望通过这些神秘而又新奇的方式,一来回溯到基督教的源头处找到更坚实可靠的信仰基础,二来实现自己征服世界的意志。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欧洲现代早期形成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进路,即实验科学。弗兰西斯·培根对这种新的科学进路做了仔细地谋划。他说,欲征服自然必先顺从自然,但他最关心的是支配自然的实际操作实践。培根热情歌颂自然法术,认为应该清除一直笼罩在自然法术身上的恶名,恢复它古代和可敬的含义。培根把自然的状态分成三种,一是正常的自然状态,二是畸形的自然状态,三是受约束的自然状态。这第三种状态就是由于技艺和人工操作造就的自然状态。培根高度重视技艺在自然科学(自然哲学)知识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技艺最能激发自然吐露出它真实的秘密,更有助于自然知识的积累。“正如在生活事务方面,人的性情以及内心和情感的隐秘活动尚且是当他遇到麻烦时比在平时较易发现,同样,在自然方面,它的秘密就更加是在方术的扰动下比在其自流状态下较易暴露。”[9] 因此,培根强调科学知识来自于对自然的干预和拷问。
培根意义下的科学不是单纯的观察,不是不声不响、不露声色的呆在一边静止的旁观,而是把事物抓起来,放到可以人为控制环境条件的实验室里来,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来对它进行反复的拷问。它不回答怎么办?你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高温、高压、高浓度或者低压、低温、低浓度。总而言之,在一种非自然的状态下,让他吐露奥秘,告诉你他的规律。所以,实验室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刺激和应激反应之间稳定规律的寻求。就是试一试对它做一个动作,看它有什么反应,再把这个动作幅度做大一点,看它再有什么反应,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刺激-应激的反应规律。实验室科学的本质就是控制论科学,目标是要控制自然,要自然吐露一些可控制的秘密。在实验室这里,现代科学的很多特征表露无遗。最基本的是可操作性,这来源于现代的求力意志,来源于现代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意志的对象。我的意志决定了必定以一种进攻的态势、斗争的意识、斗士的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世界是我用来搏斗和征服的对象。征服的方式是首先掌握自然界的刺激-应激反应规律。为了掌握这种反应规律,就需要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刺激,进行试验,记录下应激的情况,最后归纳总结出稳定不定的规律来。这里的条理、步骤和计划,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程序。实际上,也就是目标和手段最佳配置的方式。不同的目标你就要设计不同的实验程序。实验程序相当于一套拷问程序,这个拷问程序取决于你究竟想得到什么。相当于你拷问犯人,你首先要搞清楚你需要他回答哪方面的问题。不同的要求,就要采用不同的拷问方案。这个拷问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验方案。每一种实验方案都很清楚的显示自己是物理实验、化学实验,还是生物实验、心理实验,得到的是不同性质的结果。
以拷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强调,现代物理学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进步,关键是它“迫使”自然回答问题。“在对待自然的时候,理性绝不能表现得‘像一个学生,被动地听老师讲,而要像一个被任命的法官,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也说,“观察者倾听自然,实验者审问自然,迫使其显露出来。”
实验室作为一个自然拷打室,发现了无数的自然规律,使人类有效地征服和控制自然,但同时也培养出了人类和自然界的紧张关系。长久呆在实验室里的人容易生长出一颗“无情”之心,因为实验室内在的逻辑就是这样要求的:你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的立场、不能夹杂情绪和主观臆想、不能对研究对象有任何同情之心,否则,你就拷问不出自然的秘密来。
实验科学禀承的求力意志也是现代性的主导动机,因此,实验科学的精神也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流行。事实上,现代性已经把我们的生活世界改造成了一个大实验室。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已经按照实验室科学所要求的配置和结构进行了改造。今天居家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都服务于高效率的生活。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社会阶层的流动、文化的融合、新文化的创造、知识的生产,都按照类似实验室的方式去进行。现代社会科学越来越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做研究,去搞统计,去搜集数据,去定量分析。实验科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知识典范,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实验室。现代性生活必定以接受实验室背后的文化预设为前提。这个预设就是求力意志成为现代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志。
这种新型的人文理想来自基督教及其演绎和变异,而于我们中国人极其陌生。我们的文化本来并不主张一意孤行、人定胜天。佛教讲要破执,过分的张扬意志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因此,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动机来推动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活动。
[1] 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38页。
[2] 同上,第44页。
[3] 培根:《新工具》第2卷第2条,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页。
[4] 培根:《新工具》第1卷第71条,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第48页。
[5] 同上,第2卷第52条,第291页。
[6] 同上,第1卷第129条。
[7] 《法律篇》888B
[8] 《智者篇》265A
[9] 培根:《新工具》第1卷第98条,商务印书馆,第78页。
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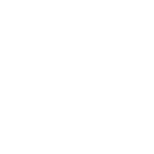


tdsrwz@163.com